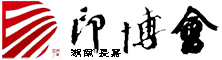近日,一篇题为《新化复印产业的生命史》的北大博士论文在网络上走红。为什么复印店老板多为湖南新化人?故事要从上世纪60年代说起。
当时,邹联经还是一个20岁的小青年,他的家乡在湖南新化县洋溪镇一个叫寨边村的小村庄。当他衣着光鲜地从外地回来时,村子轰动了。
邹联经当时在上海习得打字机维修技术。身为乡干部的堂叔一边骂他“不务正业”,一边将大儿子邹联文交给他做徒弟。
此后的几年时间里,邹联经的打字机维修技术以原子裂变般的模式,通过同宗亲戚,向整个新化县扩张。随着时代变迁,他和他的徒子徒孙们先后经历流浪维修、定点维修、二手复印机、翻新复印机等几个阶段,辐射直达全国乃至全球,新化复印产业链从此拉开大幕。
发轫第一桶金从“不务正业”开始
邹联经今年68岁,已经离开行业第一线。
广州的黄埔大道,有文印一条街。做复印设备采购销售的、图文快印的,大大小小超过了200家。店内机器闪烁轰鸣,店外停了一溜的名牌小轿车。
店里的老板都称邹联经为“老爷子”、“老革命”,饭桌上向他敬酒,说,“吃水不忘打井人。”“如果没有师傅(邹联经),就没有所谓的‘新化现象’。”邹联文说。
邹联经出生在寨边村一个手工艺者家庭。父亲是个给人修钢笔、修锁、补皮鞋的修理匠,邹联经小学没读完,就跟着父亲外出跑江湖。十二三岁时,他不但会修钢笔,还能在钢笔上刻唐诗和毛主席语录。
1964年,17岁的邹联经在杭州修钢笔时偶遇一位林姓大姐,其丈夫是上海打字机厂的工程师,邹联经由此学会了维修打字机。“那时修打字机的人很少,一个月勤快点能赚到两千元。而老家的农民从早干到晚,大约是1毛8分钱。”邹联经说。
半年后,他给家里寄来了四千块钱,盖了一座两层楼房。这在当时的村庄无异于“重磅炸弹”。
“很多人说他在外面抢,甚至是当汉奸。”邹联文说。
房子修好后,邹联经回来了。他背着一个黄色帆布包,包里装着维修的工具,上身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衣,衬衣口袋里塞着一沓崭新的十元钞票。
他打开帆布包,说他靠给人修打字机赚钱。没人相信。
邹联经于是离开村庄,从此开始“跑江湖”生涯,足迹遍布江西、湖北、河南、新疆等地,服务对象多是当地的政府机关、企事业及军工单位,因为只有这些地方有打字机。
为了获得他们的信任和尊重,邹联经给自己冒充了一个“安化红卫机械修配厂工人”的身份。有了这个“正规身份”,他住进了政府招待所。每天早上,招待所门口的小车排起长队,等他去维修打字机。
尽管如此,邹联经也曾遭遇“狼狈”。他经常正在修着打字机就被人抓走了——洋溪当地有人告他“不务正业”、“走资本主义”,稍有风吹草动就会追究到他头上。
扩散打字机修配形成“流动大军”
1971年至1977年年间,邹联经共带了三个徒弟。他带徒要求签“投师约”,内容是徒弟必须尊重师傅,师傅要毫无保留地传授徒弟等等。除此之外,必须找一个中间人为徒弟“人品”做担保——邹联文说,邹联经曾带过一个徒弟,此人是洋溪镇上一个教师的小孩,后来因为看电影别人都哭了,他却哈哈大笑,就被邹联经以“冷血”为由赶出了师门。
之所以如此看重人品,邹联文说,后来技术泛滥成灾,出现了很多偷机器零件之类的事情,“师傅算是有先见之明。”
邹联文是邹联经的同辈堂弟,年龄相差12岁。邹联文签“投师约”时,交了300块拜师钱和80斤粮票,正式成为邹联经的弟子。邹联文说,300元在当时不是小数,是父亲四处找人借来的。
昂贵的“拜师费”很快获得回报。邹联文跟着师傅去新疆多学了一个月(两个月学满),两个人一月赚了一万多元,师傅拿出400元作为给徒弟的酬劳。邹联文用其中的100元给母亲买了一双羊绒皮鞋,给父亲买了一件羊绒大衣,另外300元还了当时欠下的债务,“从此,父母再没说过师傅的空话。”
1979年,为规范“流动大军”,新化县打字机修配厂成立,邹联经出任厂长。这之后,“跑江湖”者才具备合法性。
“合是合法了,但政府并没有合理规划这个行业的发展,只是强制外出‘跑江湖’的新化人使用修(配)厂的正规发票。”邹联经说。
“那时我们在外修理‘双鸽’牌机械打字机,新化政府对此严厉打击。在城区,一见到背包的人,尤其是在火车站周边,都会上前开包查验。为了逃避查验,想外出搞修理的人想尽了办法,有的用蛇皮袋提着工具与配件,有的请妻子或母亲将配件和工具送上火车,还有的半夜三更起床,打着手电筒,从洋溪步行至隆回县城或是罗洪、金石桥等地,再乘车前往要去的目的地。现在想想,也真是苦了我们洋溪人,没有敢拼、敢闯的劲,哪里会有现在所谓的‘新化现象’?”邹联经说。
拓展从打字机维修到复印店
亲带亲,友帮友,徒传徒,邹联经的技术遍传新化乃至全国,行业形成了具有“新化血统”的链条状发展模式。
上世纪70年代末,很多新化人已经“发达”了,“洋溪邮局的汇款单像雪片似的从全国四面八方飞来,都是外出从事打字复印行业的人寄回来的钱。”邹联经说。
1980年开始,邹联经不再满足于“跑江湖”。他于1985年在上海誊影机厂学习维修誊影机技术之后,又到北京学习维修四通打字机技术。1986年,他回到湖北襄樊,开始他的“定点维修”生涯。
徒弟们也不甘示弱。1986年,邹联文学习到当时最先进的打字机维修技术后,又通过朋友花3万元买进一台二手打字机。机子是日本进口的,当时一个打字铅头都要3000多块。
在湖北枣阳,他开了一家“打字机维修店”,当地很多单位的打字机定期送来检修,不管机子坏没坏,都要给他“开工资”。与此同时,他也开始带徒弟,其中包括自己的几个同胞弟弟。
二弟邹联敏学成之后,来到广州,并由他发现了行业的另外一个新“契机”——二手复印机市场。
邹联敏说,“有一次,我在一个卖废五金的人那里发现,复印机里面那个齿轮和我们打字机上面的能通用。那时我刚出去,也没什么钱,就回家在信用社借了两三万块钱,然后买回5台机器,开始和台湾人做复印机生意。”
二手复印机市场的发现,使复印店在全国遍地开花,同时促使了国内二手复印机产业以及相关耗材产业的蓬勃发展。由此,“新化现象”形成。
2000年,尽管邹联文在枣阳的生活已经相当富足,有车有房有存款,但看到弟弟在广州的发展,他也举家搬来了广州。
邹联经早在1993年就来到广州,在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,他们都有同样的“光荣与梦想”:我有最好的手艺,这里有最多的钞票。
转型江湖“远逝”,市场还在
2002年,国家规定,以回收钢铁为主的废五金电器、打印机、传真机、电传打字机及多种复印设备,被明确列为禁止进口货物。
“这对新化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,有人就此转行,也有人将生意转入地下,新化打字复印产业一度走向低谷。”邹联文说。
邹联经在网上建了一个QQ群,群的名字就叫“二手复印机大改行”,“我呼吁大家都改行,因为这个行业已经是日落西山了。”与此同时,他认为,随着市场化、信息化的不断推进,新化文印产业的地缘堡垒也受到愈来愈猛烈的冲击。
和邹联经有同样看法的人不在少数,但也有人持反对意见。邹联文说,虽然国内市场目前已趋于饱和,政策也有限制,但这种影响只针对那些小的、散乱分布的设备耗材店和图文店。
“从过去看,不论哪个阶段,其从业主体始终是一个头脑灵活、吃苦耐劳但学历、技术水平十分有限的群体。”他说,“但现在不一样了。”
在广州,在这一行做得越来越风生水起的,是一群有一定文化知识、熟练掌握互联网,并能灵活运用社会及人脉资源的中青年人,他们懂得抱团取暖,也创造社会价值。
“靠天吃饭、靠打擦边球的老一辈们的思维是该‘淘汰’了”。邹联文望着师傅,笑着说。
去年,他的竞天图文数码快印店淘汰了一批原来的设备,从国外进口了价格高达249万元人民币的彩印机,“这在我师傅看来觉得不可思议。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买这么个设备啊?成本收不收得回?我现在不想这个,我只把产品做好就行了。”
邹联文说,师傅邹联经是他最敬重的人。2008年,邹联经东渡日本考察复印机市场,却因为性格直率、文化知识少被人骗了,几千万家产被赔光,从此隐退江湖。
“以后这个江湖还在不在呢?说不好。那我们可不可以不叫江湖?叫什么?叫市场。”他说。
据新化文印协会的数据统计,截至2010年底,新化县共有12.8万多户家庭、20.6万人口从事文印产业,分别占全县总家庭和总人口的33.7%、15.5%。其中,“新化现象”发祥地洋溪镇和槎溪镇分别有22900余户、62300余人从事文印行业,分别占两镇总家庭和总人口的71.9%、58.2%。